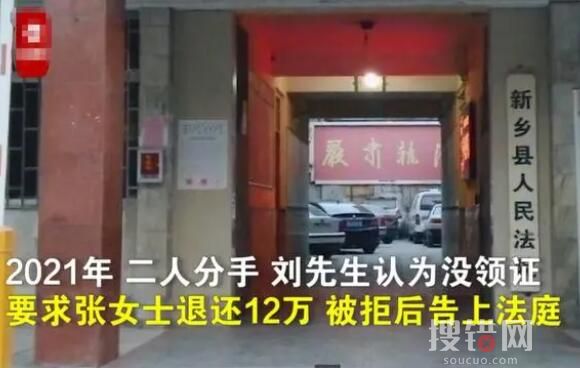高價彩禮之痛 “高價彩禮”為何近期又引關注?
導讀:高價彩禮之痛 “高價彩禮”為何近期又引關注?“高價彩禮”為何近期又引關注?背后成因是什么?各地對抵制“高價彩禮”有何嘗試?治理難點在哪?南都記者多方采訪,梳理了“高價彩禮”四大焦點
二問:“高價彩禮”背后成因是什么?
“‘高價彩禮’的成因多被歸咎于性別失衡導致的男性婚姻擠壓。”靳小怡向南都記者解釋,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,我國男女出生性別比例出現失衡,在2004年達到121,江西、廣東、海南、安徽、河南五省的出生性別比甚至超過130。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,出生性別比開始穩步下降,七人普數據顯示到2020年已降至111.3左右,也即每誕生100個女嬰,就有111.3個男嬰來到世上。據測算,男性過剩人口在3000至5000萬。
而在城鎮化進程中,人口的遷移流動又加劇了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男性的婚姻擠壓。“大量農村青年來到城市,城鄉通婚圈融合,適婚青年有了更多選擇,資源較差的農村男性劣勢地位加劇。”靳小怡表示。
易女士也有同感,“以前彩禮也沒這么高,幾萬塊就行。但現在,特別在偏遠農村地區,很少有女孩想嫁過去。這就導致本地人去外地討媳婦,包括本省的贛州,云貴地區,甚至還有東南亞國家。”易女士告訴南都記者,近期她聽說過最高的一筆彩禮高達42.8萬元,是一名“三婚”女性嫁到當地較為偏遠的農村。
這種情況還催生出許多職業媒人,他們游走在鄉間,每介紹成功一對,便能收取數萬元介紹費。“但這種職業媒人不是很靠譜,為了賺錢,還會隱瞞智力或身體有缺陷等信息。”易女士透露,“我們當地有個智力有些問題的女孩,職業媒人把她連續介紹給四位男性,女方家收到的彩禮加起來近百萬。”
靳小怡發現,在社會關系相對穩定、圈子文化濃重的鄉村社會中,締結婚姻易受到攀比、從眾心理的影響。她舉例稱,農村地區女方家庭索要高額彩禮,除了有“養個女兒不容易”的想法外,更多的考量是“別人家都要這么多,我為什么不要”。而當女方家庭所收的彩禮明顯低于普遍標準時,也會被村民議論“壞了規矩”,因此受到埋怨、排擠。
“大部分父母還是希望孩子過得幸福。城區家庭一般都會讓女兒把彩禮帶走,還會貼補一些給小家庭。”易女士認為彩禮還是得收,不收彩禮怕女兒被男方輕視。“彩禮其實體現了男方對女方和這門親事的尊重,豐儉由人。如果男方是外地人,根據雙方的習俗,商量著來就行。”
張先生也認為高價彩禮來源于攀比。“比如我們鄰居家給了20萬,我就肯定要高于20萬。因為鄰居之間會討論彩禮的事情,還會進行比較。”
另一名老家在江西的祝女士同樣表示,網傳的“天價彩禮”或許會有些“水分”,有的家庭為了面子,會宣稱自己給出了高價彩禮。但實際上,雙方父母會在私底下商討具體的彩禮數目,有些甚至還會考慮分期給付彩禮。
三問:各地抵制“高價彩禮”有何嘗試?
2月13日,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。文件在“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”方面指出,“推動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風易俗規范,強化村規民約約束作用,黨員、干部帶頭示范,扎實開展高價彩禮、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”。
南都記者注意到,這是中央一號文件連續3年點名“高價彩禮”。為移風易俗治理“高價彩禮”,全國多地開展了不同行動。
2020年5月,民政部印發《關于開展婚俗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》,指出要開展對天價彩禮、鋪張浪費、低俗婚鬧、隨禮攀比等不正之風的整治,建立健全長效機制,助力脫貧攻堅,推進社會風氣好轉,并于次年將河北省河間市等15個單位確認為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,實驗時間為3年。
甘肅、四川、寧夏等地市區(縣)直接對彩禮、酒席花費制定標準。2022年,甘肅定西市提出9條“硬核”措施,利用8個月時間對高價彩禮、人情攀比等陳規陋習進行集中整治。其中包括對彩禮、酒席“限高”,要求婚嫁禮金不超過5萬元,婚嫁活動雙方不超過2天;舉辦婚事酒席不超過20桌,在城區每桌不超過880元,在農村地區舉辦婚事每桌不超過480元。
同年7月,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發布的《移風易俗條例》提出,按照傳統習俗確需給付或者收受婚嫁彩禮、禮金,彩禮的標準和禮金的種類、標準應當遵守村規民約(居民公約)等相關規定,要自覺抵制索要高額彩禮、禮金或者利用彩禮、禮金干涉婚姻自由;操辦婚事時應控制婚嫁宴請對象、范圍、次數、隨禮標準及接送親車輛、人數和聚餐(宴席)規模、標準等。
今年2月,寧夏涇源縣也出臺《進一步推進移風易俗助力鄉村振興的實施意見(試行)》,提出彩禮最高不得超過6萬元,并逐年下降,酒席不超過10桌,人情禮金不得高于200元。此外,加大“零彩禮光榮,高彩禮丟人”宣傳力度,形成抵制高價彩禮的社會氛圍。
而在2022年9月,江西廣昌縣就曾為“零彩禮”的10對新人舉辦移風易俗集體婚禮,這場婚禮在線直播,觀看量超4萬人次。一位參加婚禮的新娘表示,“這么熱鬧又有儀式感的婚禮,是多少彩禮都換不來的。”
同年11月,在江西省進賢縣人民廣場,進賢縣委宣傳部、縣婦聯、縣民政局等單位聯合舉辦第二屆“樹文明新風不要彩禮要幸福”集體婚禮,現場16對新人參與,共同倡導“抵制奢靡之風,反對高額彩禮”的文明新風之舉,用實際行動踐行移風易俗文明新風尚。
“政府對于這種婚育新風的宣傳和倡導還是非常有必要的。”靳小怡向南都記者表示,觀念的扭轉對于抵制“高價彩禮”至關重要,地方政府因地施策、逐步完善與細化相關措施,充分考慮不同鄉村的經濟社會狀況、村民文化素質等因素,對彩禮標準進行具體地規定,“能夠實現精準打擊和治理”。
劉建生也認為,“限禮”標準、村規民約(居民公約)等移風易俗措施對于降低婚嫁成本、形成新風尚能夠發揮一定作用。
四問:“高價彩禮”治理難點在哪?
多措并舉之下,部分地區整治“高價彩禮”取得成效。2022年底,民政部召開全國婚俗改革經驗交流電視電話會議,指出各實驗區從開展婚姻家庭輔導、倡導簡約適度婚俗禮儀、培育文明向上婚俗文化、傳承良好家風家教四個方面入手,“細化實施方案,聚焦主題主線,采取有效措施創新試點,較好完成了階段性實驗任務”。
河北河間市介紹稱,該市被確定為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后,自2021年4月以來,全市共辦理新婚登記4726對,其中“零彩禮”“低彩禮”占比88%,每樁婚事花費比之前平均減少7萬至15萬元。

2021年5月20日,河北省河間市在瀛海公園舉辦“零彩禮”公益集體婚禮,26對新人身穿中式傳統婚服執手入場。
日前,甘肅定西市也公布了高價彩禮的治理情況,據不完全統計,治理高價彩禮推動移風易俗培育文明鄉風攻堅年行動自2022年6月份啟動實施以來,當地70%的出嫁方彩禮控制在0至5萬元以內,平均為4.9萬元,比行動前下降了10.9%。
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也表示,移風易俗專班運行以來,全州共報備紅事991起,白事2527起,共制止10萬元以上彩禮528起,涉及金額7010萬元,收集村(居)民從簡辦理婚喪事宜的典型案例263起,群眾“不愿收、也不愿送”的氛圍已初步形成。
然而,根治“高價彩禮”難題,依然無法一蹴而就。靳小怡向南都記者分析,“人口是一個大的慣性系統,未來可預期的二三十年內,我們的婚姻市場供需都是不平衡的,彩禮問題甚至可能更加嚴重,這是一個長期的綜合性的治理過程。”
靳小怡認為,“治理的底層邏輯是承認愛情是婚姻的基礎。”她在調查中發現,“高價彩禮”也并不能保障婚姻幸福,“我們發現部分收取高額彩禮的家庭,婚姻質量不高,一個是離婚的意愿比較高,另外婚內家庭暴力發生率比較高。”她表示,應倡導回歸婚姻的本質,將其建立在彼此了解和真實情感之上。此外,還應提升農村人口教育水平,加大中西部農村居民教育投入,令其能夠接受正確的婚戀觀。
“ ‘高價彩禮’背后的另一個問題,是農村‘光棍’增多。”劉建生告訴南都記者,“有的男性四五十歲還是單身,寧愿多花點錢也想成個家。”
靳小怡也觀察到,人口性別結構失衡難以快速轉變,欠發達農村地區大齡未婚男性的生存發展權益應受關注,“比如通過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與支持力度,滿足欠發達農村地區大齡未婚男性的基本生活需求和養老需求,營造更寬松的社會環境,減輕對他們的社會排斥。”
此外,她表示,還應加強教育、就業、醫療、社保等優質資源在城鄉間、區域間的合理配置,促進中西部農業轉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鎮化,避免人口遷移流動加劇男性婚姻擠壓。
從根本上破解“高價彩禮”難題,劉建生認為,一方面政府要加強引導進行移風易俗;另一方面,必須加快推動鄉村振興,不斷縮小城鄉差距,“讓年輕人愿意留在鄉村發展,讓更多男女青年愿意在鄉村安家落戶”。
-
 年薪30萬女生轉行賣快餐 原因竟是這樣實在是太意外了2017-09-01 14:33:32年薪30萬女生轉行賣快餐 原因竟是這樣實在是太意外了。近日,廣東深圳。97年的王女士自考成人本科,2017年畢業,2020年進入大廠從事社群運營工作,年薪在20-30萬。
年薪30萬女生轉行賣快餐 原因竟是這樣實在是太意外了2017-09-01 14:33:32年薪30萬女生轉行賣快餐 原因竟是這樣實在是太意外了。近日,廣東深圳。97年的王女士自考成人本科,2017年畢業,2020年進入大廠從事社群運營工作,年薪在20-30萬。 -
 醫院有位患者叫熊貓是真熊貓 原因竟是這樣實在是太意外了2017-09-01 14:33:32醫院有位患者叫熊貓是真熊貓 原因竟是這樣實在是太意外了。什么人居然名字叫熊貓?3月1日,一則CT信息單引發熱議,在病人姓名一欄赫然寫著“熊貓”。
醫院有位患者叫熊貓是真熊貓 原因竟是這樣實在是太意外了2017-09-01 14:33:32醫院有位患者叫熊貓是真熊貓 原因竟是這樣實在是太意外了。什么人居然名字叫熊貓?3月1日,一則CT信息單引發熱議,在病人姓名一欄赫然寫著“熊貓”。 -
 3月2日看金星與木星浪漫相擁 相擁真相曝光簡直太驚人了2017-09-01 14:33:323月2日看金星與木星浪漫相擁 相擁真相曝光簡直太驚人了。絕大部分時間里,如果不算太陽和月亮,人們肉眼可見的星星中金星和木星的亮度排名分別為第一和第二。今年2月底到3月初的這段時間,傍晚時分的西方天空
3月2日看金星與木星浪漫相擁 相擁真相曝光簡直太驚人了2017-09-01 14:33:323月2日看金星與木星浪漫相擁 相擁真相曝光簡直太驚人了。絕大部分時間里,如果不算太陽和月亮,人們肉眼可見的星星中金星和木星的亮度排名分別為第一和第二。今年2月底到3月初的這段時間,傍晚時分的西方天空 -
 一夜3次地震 全球進入地震活躍期? 原因竟是這樣實在是太意外了2017-09-01 14:33:32一夜3次地震 全球進入地震活躍期? 原因竟是這樣實在是太意外了。2月16日,中國地震臺網中心預報部高級工程師韓顏顏發文表示,我國是世界上大陸地震最頻繁、地震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。
一夜3次地震 全球進入地震活躍期? 原因竟是這樣實在是太意外了2017-09-01 14:33:32一夜3次地震 全球進入地震活躍期? 原因竟是這樣實在是太意外了。2月16日,中國地震臺網中心預報部高級工程師韓顏顏發文表示,我國是世界上大陸地震最頻繁、地震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。